初秋悄至,凉风吹动树梢,拂卷荒疏草木。
魏征的身体如落叶日渐凋零,入秋以来久卧病榻,仍强撑着撰疏上奏李世民,道他未能尽太傅之责,道李承乾误入歧途自己有着不可推卸的过错。
他似乎天生不擅长教好太子。
魏征望着窗扉外飘渺天穹,游浮白云,这般嘲弄地苦笑。
窗未拢闭,吱呀作响,卷动案上未毕的奏疏,吹阖他的瞳目。
意识朦胧间,他恍然听得耳畔有哭声渐起,有人攥住他的手腕,含泪道朕失玄成,如失一镜矣。
原来他辗转半生,还有人将他视作明镜。
魏征不禁微笑。
“玄成劳苦,但需容孤从长计议。”他献十策于李密,却未能见纳其一。
他怏怏,又拜见了李建成:“秦王功高,太子应早为之计。”
那人照例不以为然:“本宫为嫡长,有何惧哉。”
最后他在那个日光朗照的仲夏见到了李世民。
他向王座上的青年顿首:“愿陛下令臣作良臣,而非忠臣。”
青年笑道:“此二者有何分别乎?”
“良臣既有美名,又可使君主显扬,百姓安居乐业。而忠臣舍生取义,君主却怙恶不悛,自身丧国夷家,只余空名。”
庭前月下,君臣对酌,君王饮过他所酿甘醪龙颜大悦,遂挥毫赐他一首诗歌:
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薤。
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
题下有注,魏征善治酒,有名曰醽醁,曰翠涛,世所未有。
然而君王与他的明镜之间,又有几个千日,复有多少十年。
“不要离我而去——”
一声凄切的呼唤,那双手攥得他弥紧,仿佛要将他魂魄强行留在尘世,可他还是化作一缕轻烟,挣脱归于上空。
这艘浮沉半生的小舟终究飘荡至天际,湮没于层层叠叠的云雾之中。
但他此刻终于发觉,欲作忠臣良臣,原来皆仰赖于君王。
原来那年的仲夏是如此明亮,近乎令他眩目,让他怀念至今。
而世所未有的,又岂止是他所酿的醽醁翠涛。
乃是一生谏诤数十万言的贤相,与欣然嘉纳那数十万言,又谑道卿甚妩媚的明君。
此去山长水迢,本不必相送。
但他还是将远去的小舟折返,桨动水波,光阴倒溯,他仿佛再次回到了那个夜晚。
风声吹拂松涛,天边明明如月,大唐的丞相最后一次理袍振袖,顿首拜别:
“臣魏征,此生不愿为忠臣,只愿作陛下一人的良臣。”
*
贞观十七年,魏征病逝。
李世民颓唐地倚着胡床,望着发顶二尺之距的铜制鸟笼,其间已然空荡无一物。
纵再无劝谏他休得沉溺玩物的诤臣,再无人阻碍他赏鸟,然而他已不再有兴致。
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而今明月清辉,又能与何人同坐。
他从未如此懊悔,为何他偏偏是最年轻的那个。
感情最充沛之人,偏偏要眼睁睁目睹亲朋旧友一一离世,独留他一人高居庙堂,一片落寂。
然而未有多久,他再次失去了至亲。
他失去了他曾寄予厚望的爱子与女儿。
一夕之间,李世民仿佛性情大变,他开始崇信方术,祈求益寿延年,为此不惜折损早已亏殆的身体。
甚至不顾群臣劝谏,执意亲征高句丽,落得开边未已穷兵黩武的讽嘲。
群臣摇首,私底议论时,难免叹曰圣人春秋已逝,终难免犯些糊涂。
长孙无忌道,非为糊涂,这便是他的苦衷。*
李世民是太心急,早年累积的旧疾此刻席卷而来,侵蚀他的寿命。
他急于为稚弱的李九留下一个清平盛世,他生怕雉奴会对异族的朝三暮四束手无策,于是他试图除去所有后顾之忧,尽他所能让李九做好一个守成之君。
皇帝开始将重任一以委之于长孙无忌,让他在最后三年累封门下、中书两省长官,自此为群相之首。
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病故,不久李靖辞世,他亦病势沉重,卧榻不起,御医皆惶恐言回天乏术。
君臣泪落如雨,相顾无言,李世民又令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叮嘱遂良务要留意。
他说,辅机身份特殊,功劳彪炳,不可令其遭逢小人谗害,卿需千万保护好他。
褚遂良含泪答诺。
贞观二十三年,帝崩于含风殿。
至此,君臣一梦,死生西东。
*
后来贞观与开元俱成了烟云,安史之乱终了,永泰年间,吐蕃乘乱攻陷长安。
代宗令郭子仪率军击破吐蕃,历经动荡的唐室,至今终于收复故土。
山河破碎,长安寥落,昔日九成宫的墙垣颓圮荒败,唯独城春的草木仍旧蕤深。
又是一年上元,有人自长安鬼市淘得一部古籍,乃晋代泰始年间刻本,如获至宝,当即购回家中。
正翻页时,一张陈旧的笺纸掉落。
那人疑惑捡起,却见其上红漆褪色,唯墨迹尚存。虽以胡语写就,然而字体清丽,应是一异族女子所留。
购书人邻居乃一世代久居京城的博学宿耆,于是他当夜敲其门户,执灯相问。
邻居遂以官话念予他听:
一愿与辅机终老。
二愿哥哥长命百岁。
最后一行字已然模糊,须经细察,方依稀能从笔画中辨清。
他却闭口不再言语,稍顷,瞳中似蕴积了红痕。
购书者见他陷入沉默,蹙眉追问:“第三个愿望究竟是甚么?”
却未听见回音,他惊诧再看,苍髯白发的老者竟已怆然泪落。
那年元夕,灯火阑珊,少女眉目如初,正与身畔友人执笔许愿。
「阿盈怎有这么多愿望?」高鼻深目的胡人女子惊讶地瞥向少女手中的祈福红笺。
少女摸了摸鼻尖:「我一共许了三个,我想许的越多,总有一个会实现的罢。」
她仰起头,将红笺郑重地挂于树梢,系紧绳结,慢慢阖上瞳眸,轻声呢喃祈祷。
*
显庆四年春,许敬宗诬长孙无忌谋反,李治竟不问所由,径自下诏剥夺官爵,流放黔州。
长孙无忌未作出任何反应,连半分质问也无,平静地接受了意料之中的结局。
如他所想,这一日早该到来。
流放地的斗室孤陋清简,举目除却一方矮榻,结网窗牖,此外别无长物,倒有了当年随李世民征战时军营的影子。
伴他流放至此之人,只有二三随从,其中有一老仆,常见主人凭窗遥眺远方,于是忍不住出言相劝:“郎君休得惆怅,浮生本就如梦,万事皆空,郎君年过半百竟仍是看不穿么?”
长孙无忌闻言苦笑,他如何能知自己惆怅的是甚么。
非为过往绮丽,眼下岌岌处境,更非为逝去如水功名。
乃为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那里恍如隔着这千万重山峦叠嶂,漂泊雾影掩过数不尽的楼台宫阙,雕梁飞甍,茫茫然空余遗响。
他竟然开始庆幸,庆幸她已经去世了,否则她看到自己如此狼狈,被扣上谋反如此荒谬的罪名,连长安也成了回不去的泡影,宗族俱流放岭南,必然会伤心难过。
他怎舍得让她难过。
仿佛一闭目,她的面容仍清晰浮现,可细算来,她离开他的时日竟将比他们陪伴的光阴还要长了。
少年夫妻,终究未至白首。
他唤老仆取来纸砚,提笔舐墨,点一盏昏黄枯灯,借着萤萤微光,伏案默书经文。
末路孤寒,他惟能以此作为寄托。
老仆长叹一声摇摇头,放轻手足离去。
室内空留一人,长孙无忌疲惫已极,眼前京洛旧游故人途经停驻,纷纷乱乱,面目明彻。
「我知辅机欲避嫌之心。」彼时已显病态的帝王凝望着他,眼眶濡湿,「可如今朕唯有辅机可以托付,你若执意不肯,朕的大唐与雉奴不知何去何从。」
自古顾命权臣能善终者有几人。
但纵然二人俱通熟史书,李世民亦只能将此重任强加于他,而他亦接受了。
李世民不舍又能如何,他竟退无可退。
而长孙无忌为了大唐,为了十余岁时倾心相知的李二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士为知己者死,虽万死也难辞。」他俯身再拜,尽力宽慰着挚友与君王,「臣长孙无忌,谨遵圣令。」
可永徽终究不是贞观,此时的长安亦非彼时的长安。
他到底还是未能实现李二郎的期望。长孙无忌想道。
此时眸前天河流转,脚步又踏入一处陌生之地。
这是一座偌大的屋室,其间充塞千百册卷牍,青年男女端坐于桌椅间,俱各专注阅览。
他在这间貌若藏书室的处所向前踱去,忽地目光定住一人,旋即停了脚步。
少女正伫立窗台前,倚着雪白墙壁,手中捧着一部厚重的书卷。
他低首视去,隐约窥得扉页“唐书”二字。
他就这般在晨光熹微之中,静静地,静静地凝视她读着自己的结局。
她到底还是会难过。
他走上前去,想为她拭去眼角泪痕,可指尖在触碰到她面庞的一瞬间,刹那烟消云散。
“王世充坚守洛阳不出,连月僵局,辅机可有妙计?”
军营外朔风呼啸,远处洛阳城固若金汤,隐约藏入乌云之中,营帐中的青年忧虑问策。
“破一城,当先行教化,辅机所言甚是。”
青年听罢陈词,霎时舒展双眉。
“我绝非坐以待毙懦弱宵小,辅机一语已定我决心,卿等勿再言矣。”
那一夜,青年破除所有犹疑,目中透出坚毅,缓缓按紧腰间剑柄。
他正惘然中,身后忽然传来一道欢快唤声。
“辅机今日何不与我赴芙蓉园观花赏酒,午间共垂钓于昆仑池乎?”
他旋身相视,李二郎着美衣轻裘,于天际朝阳处,向他纵马驰来。
“辅机怎生有些拘束。”李二郎勒马,见他面容怔忡,甚至静立半晌未有反应,不由扬鞭大笑,“莫忘了,我们该是一世知交。”
他启唇欲答,语未出口,眼前景象忽又迁移,再度变作一座空旷的天地。
三五男女生正围聚于李盈身旁,观着她在宣纸上落墨挥毫。
长孙无忌已经很久没有见她写字,于是敛袖上前立于案旁,望着她在砚中仔细研墨。
“盈盈的书法刚又得了奖,快给我写一幅带回家收藏,说不定以后成了大书法家,那可就千金难买了。”女孩笑语钻入耳中。
李盈不好意思地笑笑,她向来惯于满足他人愿望,当下也不推辞,从旁换了张新纸。
她安静地提笔蘸墨,才欲落笔,蓦地,似乎感觉到了甚么,抬首望向桌案前方,可就在长孙无忌以为她看见了自己时,她又低下头,握紧了笔杆。
长孙无忌不禁自嘲,异世相隔,且自己如今尘霜满面,早不是她熟悉模样,他岂敢有这般奢望。
女孩得了李盈才写罢的行楷,如获至宝地捧在手中,俯身将痕迹吹干,轻声将笔墨读与旁人: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女孩不禁笑道:“盈盈好高的境界,就连写书法也选这句话,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对遗憾释怀呢?”
……
他怎可释怀。
他如何能够释怀。
她愿望未了,而他不得善终。
他于是想,自己这一生何其荒唐。
倏尔,啪嗒一声,一双手剪亮烛芯,案前灯花忽然醒目几分。
“怎么会荒唐呢。”
李惜愿发愁地摸摸脑后,抬手为他拭去泪痕,轻声道:“这便是我们的命运。”
她如此安慰着他。
可长安的夜晚虫鸣阵阵,他不曾想过分别。
粉襦、绯裙、冰蔗浆,回不去的初夏好时光。
他想,如若再来一遍,他仍然会赴渭河彼端的长春宫谒见。
但贞观不会再有赵国公长孙无忌,永徽也没有权倾朝野的长孙太尉,大唐唯有李二郎的至交,李小六的辅机。
从此他将拜别君王,赁一叶小舟逐流而下,途经哪儿停哪儿,然后与李小六在江南看她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我在等哥哥接我回家。」
可是贞观三年的秋天,李小六到底一个人也没有等到。
“若你尚在我身旁,我便不会承诺二郎。”
他从未料及,竟然有一日他能剖白至此。
李惜愿却笑了。
“我不信你的话。”她支颐凝望他的胸口,摇了摇头,“我看见了……你的心。”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一滴泪倏尔自眸底滑落,沾湿了他恍若雪色的白发,淌过衣襟,终归消弭于尘土。
原来这是他的最后一场梦。
原来她入梦而来,是为了劝他释怀。
而今,他依旧在梦里孤身一人。
须臾间,那些盘旋许久的挣扎纠缠俱化作飞烟一缕,远去天边,飘荡如鹤,随风解脱他滞锢已久的魂魄。
终于,从远方飘来的冷寒空气重回胸腔,他仿佛再次得到了喘息。
*
贞观二十三年的雪落去十载,长孙无忌逝于黔州。
直到最后,他也没能回到长安,而大唐,亦再回不去贞观了。
而他此时终于发现,大业十二年的那碗肉桂乌梅饮子其实很酸,李惜愿想寄给兄长的那封家书也未能有力气写完。
原来,他们终究甚么都落了空,甚么都成了遗憾。
就像那年元宵月圆,少女许下的最后一个心愿。
——三愿,愿长安永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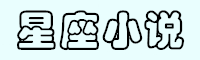 【星座小说】XINGZUOXS.COM【星座小说】
【星座小说】XINGZUOXS.COM【星座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