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的结果将于十日后在含元殿上昭告天下。
顾宁熙征召八名翰林院学士,于宣政殿中一同阅看士子答卷。
二百余份策问,每一位士子的文章都有三至四位学士判定,力求公允。
顾宁熙每日守于宣政殿中,连日来一颗心尽数扑于此。
午间光景,又是半日的忙碌,御膳房已备好午膳。
翰林学士们用过膳,可在各自的厢房中休憩一个时辰,未时再继续评卷。
这十日里,八位翰林学士不得归家,宫中另行供给住处。每人单独一间卧房,禁军时而巡视,以防他们私下有何交集。
顾宁熙则抽闲暇回了一趟坤宁殿,阿姊已经在等她。
宫中三月的宫务顾宁婉如数处置妥当,最终的账目移交顾宁熙。
她拨了拨茶盏,道:“我这一份尚宫的俸禄,没有一分一厘是白得的。”
顾宁熙笑起来:“多亏了有阿姊。”
春闱过后她实在分身乏术,好在后宫风平浪静,她便暂且将宫务丢了出去。
“陛下不在吗?”
“他晨起去仁智宫了。”
顾宁婉点头,便可以在坤宁殿中多留一会儿。她道:“殿试快有结果了罢?”
“是啊,最快后日就能排出次序。”
顾宁熙留心着考生的籍贯:“此番入选的多数还是世家大族的子弟,寒门士子人数不多,且殿试前的名次多靠后。”
科举考生来源有二,一为官学学生,即出自国子监、弘文馆与崇文馆;二为乡贡,由地方州府考核当地学生,合格后将他们送往尚书省参与礼部的科举考试。
其中官学学生占了九成以上,顾宁熙也曾是国子监出身。
官学学生大多家世不俗,依靠祖辈荫封,资质平平者也可入国子监读书,再占据一个科考名额。
为真正地选贤举能,由天观二年始,顾宁熙想逐步提升寒门士子在科举中的比例,打压世家大族,尽可能给有学之士一个公允的机会。
新的人才步入朝堂,大晋方能更欣欣向荣。
此路艰难,任重道远,绝非一旦一夕之功。顾宁婉道:“那便要先兴州学与县学。”
平民子弟总要有入学读书的良机,才能再谈科举。
户部能够拨付银两兴修学堂,地方州县也能筹措出银子。顾宁熙道:“不单要兴学,还要兴女学。”
昔年懿文皇后与姚皇后同办了惠文堂,专供女子读书。
惠文堂虽未成气候,却开了大晋先河,有例可循。
朝廷既要不拘一格录用人才,寒门子弟可以,女子当然也可以。
中原大地饱经战乱,数不清的男子战亡在前线,家中往往是他们的母亲与妻子下地耕种,撑起门庭。
正因如此,本朝民风开放,女子的地位更胜于前代。
朝中英才短缺,新的国之栋梁又何必只向男子中寻?
“阿姊可明白我的意思?”
女子能入学,当然也能科考。先从世家大族的女郎开始,顾宁熙同时好奇,不知寒门士子与世家大族的女儿,权贵们更能接受哪一方入朝。
女子走出后宅另博一番天地,纵然如今还如天方夜谭一般,但十年后、百年后,只要开始有女子能真正站上朝堂,后继者便会绵绵不绝,继往开来。
顾宁熙会为之努力,她相信她的长姊能为先导,顾宁婉亦信任着她。
姐妹二人相望而笑。
若非亲眼所见,他还是不愿相信素来在他们面前乖巧孝顺的幼子竟潜藏如此狼子野心,妄图挟持君父,犯上作乱。
“陛下,淮王殿下来向您请安。”
太极殿内,李暨恭敬通传。东宫被废,朝堂风云突变,陛下心情大起大落。李暨专门叮嘱太极殿上下,当差务必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今日的午膳陛下只用了几口,太医为陛下换了安神开胃的药方,日日都来为陛下请脉,望陛下保重龙体。
“就说朕睡下了罢,”明德帝暂不愿见淮王,“去告诉诚钰,让他多去陪陪他的母后与兄长。”
“是,陛下。”今日并非休沐,但趁午间悠闲,顾宁熙悄悄从昭王府溜出去一阵也无伤大雅。
表兄已经在茶楼等她,他才从西山兵营换防归来,这几日都在家中休息。
陆陆续续看了两月的宅院,他们已经选定了兴庆坊的一处院落。
原本他们一同凑了三百贯钱,但这个价位的宅院顾宁熙总没有挑到合心意的。原本想着将就先买一处,但商行的人近日带顾宁熙相看了这处新院子。房主南下经商周转不开,急于将宅子套现,统共三进的院落只要价四百贯。
这处宅子顾宁熙仔细看过两回,无论是从位置或是布局都挑不出瑕疵。不仅南北开阔,通透敞亮,西侧还连了一处小花圃。尤其顾宁熙检查过屋中的梁柱,用的木材都非常扎实,并不曾偷工减料。且这处宅子平日少有人住,没有太多磨损。
顾宁熙是工部出身,买房置产乃是行家,孟庭相信她的眼光。连商行的人都知道这位年轻的小郎君不好糊弄,不敢在她面前耍滑头,推荐过来的宅子都不错。
“与其用三百贯买一处两进的宅子,倒不如花四百贯选这座三进的院落。表兄觉得如何?”
顾宁熙拨着珠算盘,怎么看都是后者更划算些。
孟庭眸色温和:“依你便是。”对方开价四百贯,他们这些日子与房主反复议价,商行的人也从中斡旋。最后约定双方各退一步,三百七十贯。
顾宁熙和孟庭各自添了余钱,总共能拿出三百五十贯。
对面全要现银,且是一分都不肯再让的。顾宁熙掬了捧清水,知道又是顾宁铮那个草包在作怪。他惯爱使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小手段,损人又不利己。
也是她自己行事有欠妥当,仗着今日不必当值,昨日睡得太晚了些。
看眼下这个时辰,昭王府中的宴席都快结束了。
顾宁熙揉了揉眉心:“先替我更衣吧。”他也不知今夜为何心绪不宁,闭上眼便是元乐酒醉的模样。
后半夜月光倒好,照亮了寝殿一角。
两日来送入昭王府中的寿礼都已造册搬入库中,寝殿北面的博古架上唯独新添了一样物件。
檀木所做的水车摆在中央最显眼处,二十三个小竹筒在机关推动下依序转开。
新升至最高处的竹筒,上面雕的是万回。这位能够预卜休咎、排难解忧,保护行旅之人回乡团聚的神仙,似乎也解答不了昭王殿下今夜的困惑。
“是,大人。”
要穿哪套衣裳顾宁熙昨日便已选好,吟月依她的吩咐,取来那套天青色绣折竹如意纹的锦衣。
顾宁熙在铜镜前自挽了发,束上一枚碧玉冠,簪了一支青玉竹节簪。
这支玉簪是及笄那年母亲替她簪上的,今日是第二次戴。
收拾妥当,顾宁熙仔细包好了给昭王殿下的生辰礼。临出屋子前,她又对着铜镜照了照。
皓日当空,顾宁熙抄近道预备从人少些的后门出府。奈何今日实在运道欠佳,都这个时辰了,竟然在花苑凉亭中遇见了对弈的祖父和父亲。
顾宁熙硬着头皮上前见了礼,宣平侯察觉到不妥:“怎么这个时辰在府上,昭王府的席散了?”
顾宁熙含糊道:“孩儿……有事耽搁了,三弟便先去赴宴了。”
宣平侯蹙眉,顾老侯爷拈了一枚棋子:“那便去罢,好生向昭王殿下赔罪。”
“是,孙儿明白。”
顾老侯爷开口,宣平侯当下自然不会再多说什么。只在顾宁熙离去后,他摇头道:“这也太没分寸了些。”
次子已经足够不让他省心,科考频频落第,至今尚是白身。宁熙又夹在东宫和昭王府之间,进退两难。
顾老侯爷淡淡道:“他们兄弟不睦,你还不调停吗?”
三郎是天资不足,延请多少名师教导都不见长进。偏他还是长房独子,将来袭爵,阖家都得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让人看不到出路。
“至于宁熙这边,”顾老侯爷道,“只要昭王殿下不计较,你又何必再追究。”
“父亲的意思是——”
顾家多年的掌舵人,如今到了古稀之年,做事反而更想听凭直觉。
他落下一子,昔年道士给宁熙的批语犹在耳畔。
孟氏产子后,长房的所作所为当然瞒不过他。只不过当时有大师断言在前,他亦觉得男孩入朝会更有一番作为,所以他才默许了长子的隐瞒,将这个孙辈假充作男孩教养。
然现下想想,就算是得遇明主,在朝位极人臣,只怕也配不上“三甲天上贵”的龙凤命格。
顾宁熙也知道这个价格太过划算,错过这个村便没有这个店了。
皇都地价已经在看涨,这月若是不能定下,没准下月宅子的价格就飞涨了。
顾宁熙行事很是干脆:“我已经告诉了商行,近日可以约房主来订契。”
至于短的那二十贯钱,她道:“我有办法。”胸有成竹的模样,孟庭下意识便信她。
买宅院是她的主意,表兄二话不说能陪二百贯给她,顾宁熙已足够领情。
此事隐秘,他们都瞒着家中人,不愿两家的长辈为此节衣缩食。
二十贯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顾宁熙脑中过了一遍数目,一时半会儿还真凑不出来。
她所有的积蓄,包括俸禄,包括这几个月卖字画的银两,还有祖母寿宴上得的金银锞子,都如数填进了那三百五十贯中。
她在表兄面前之所以如此说,是已经打定主意要向旁人借这二十贯。
表兄撑着孟家门庭,是孟家的主心骨,每月林林总总的开支总归多些。而她只是顾家的小辈,管好自己就可。由她去借钱,身上的担子肯定轻些。
顾宁熙盘算清楚,回到昭王府时正好赶上当值的时辰。
修改后的畅清园的图纸整整齐齐摆在她的桌案上,顾宁熙休息了一会儿,便抱着图纸去求见昭王殿下。
不知怎的,他对这处温泉别院的修葺很是上心,隔出几日便让她送图纸去一观。顾宁熙瞧哪怕是前段时间昭王府的修整,也没见昭王殿下分出这些心思。
书房中,陆憬手边尚余些政务。
平日里孙敬是不会搅扰的,但此刻他禀道:“殿下,顾大人在外候见。”
“让他进来吧。”陆憬不假思索,将手中阅了一半的公文先搁置一旁。
孙敬含笑去传话,迎了顾大人入殿。
日升月落,天边已现鱼肚白,巍巍宫城在晨曦掩映下更见庄严恢弘。
卯时将近,含元殿前的广场上,文武臣工陆陆续续汇聚于此。
今日是新科进士入朝谢恩的日子,朝堂上很快便有新面孔。
时有佩刀的禁军在此巡察,铠甲上的寒光与阶前宫灯交映,尽显朝会的肃穆。
含元殿后的澄仪殿,惯例是供帝王早朝前稍作歇息。
陆憬执了顾宁熙的手:“可紧张?”
顾宁熙一身玄色五彩袆衣,十二花树冠分毫不乱,闪着花彩。
她诚实地摇头,原本昨夜还有些辗转难眠的心绪,在踏入前朝时尽数烟消云散。
她观望着澄仪殿中陈设,一切都令她感到莫名的熟悉。
她低头笑了笑,甚至会觉得身旁人多余。
元乐如此气定神闲,陆憬只能将安抚的话都咽了回去。
他其实想告诉她,大晋朝堂皆在他掌控中,有他在,她不必担心朝臣的非议与反对。
前世未尽的结局萦绕在他心头,她说该向前看。
既再续了前缘,他想将最好的一切都给她。
朝霞层层叠叠铺陈于天际,沉浑的钟声回荡在宫城,消散在旭日东升的光晕中。
含元殿的殿门打开,百官分作两列,持笏肃然踏入金殿。
今日的朝会本就因新科进士入朝而显得不同寻常,然玉阶上的变化,更让大部分文武臣工始料未及。
中央依旧是那张金丝楠木所制的帝王龙椅,其后设一道日月山河屏风。而御椅右侧七步远,新设一张楠木宝座,宝座前有一道珠帘相隔,此刻随风微微晃动。
而宝座的主人是谁,答案呼之欲出。
邻近的官员们交换着神色,目光中似有千言万语,但谁都没有率先宣之于口。
等待的光景因那宝座的出现显得尤为漫长,直到御前的总管高声唱和:“陛下驾到,皇后娘娘驾到!”
一切尘埃落定。
文武百官整肃衣冠,先行三跪九叩之礼。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顾宁熙沉静落座,俯瞰着大晋文武百官们。
似有一幕幕场景在她眼前交织,最后如数化为朝堂模样。
“众卿平身。”
百官归于原位,朝议并未即刻开始。殿中陷入静默,似是君臣间在无声对峙。
玉笏后的臣工屏气凝神,五息,十息。皇后娘娘临朝,中书令没有开口,门下省侍中没有开口,尚书省二位仆射没有开口。明德朝的元老,太上皇最信任的司空裴大人也没有多言。
谁都不愿去做那出头鸟。
陛下平定四海,即位以来整顿国政,削陆氏王爵如切菜一般,吏治更是毫不徇私。
朝堂的中流砥柱们都缄默不言,谁还敢站出来率先忤逆陛下。
甚至有人存了侥幸,兴许皇后娘娘只是到朝堂一观,不会长久。
顾宁熙鬓边流苏轻晃,心中亦在想,这十二树花钗太过沉重,日后得换一顶轻便些的凤冠才好。
于是朝会照常开始,鸿胪寺卿传唱了殿试名次,扬声道:“宣新科进士入殿!”
迎着朝阳,意气昂扬的新科进士们阔步踏入大殿。
相较于朝堂上百官,再度见到珠帘后的皇后娘娘,他们反而接受许多。
一甲三人领着身后的同年们齐声叩拜,其中榜眼声音尤为洪亮。
他出身平平,殿试之后,他的名次由百名开外跃至第二,光耀门楣。
新科进士之中,如他一般的人不在少数。
殿试于他们最为公允,他们无比感激加试了这一场,更感念陛下与皇后娘娘恩德。
高台上,顾宁熙与陆憬并肩而坐,遥望着朝堂上的新生力量,
云蒸霞蔚,朝霞满天。
大晋江山终将会迎来一番新气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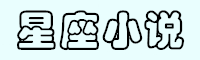 【星座小说】XINGZUOXS.COM【星座小说】
【星座小说】XINGZUOXS.COM【星座小说】